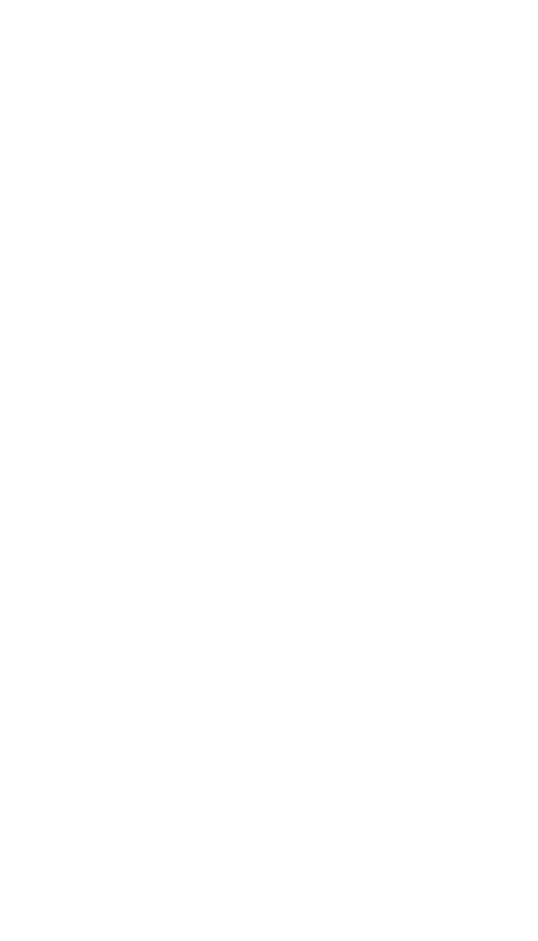網上剪接大師班 ── 馬修
時間:2020年2月27日 (日) 15:00 - 16:30
地點:Zoom
嘉賓:馬修(法國剪接師,剪接作品有《天註定》、《山河故人》、《江湖兒女》等)
文字紀錄:岑依霖
文字校對:鄺曉恩
剪接師
馬修 Matthieu LACLAU
馬修,法國剪接師,常駐台北,活躍於華語電影圈,與金獅獎、金馬獎大導演賈樟柯合作無間,共同作品有《天註定》(金馬獎「最佳剪輯」獎)、《山河故人》、《江湖兒女》及《卡夫卡的K》等;馬修參與多部劇情、紀錄片剪接,早年曾任攝影,亦致力培育新銳導演,作品包括《Hello!樹先生》、《傷城》、《革命是可以被原諒的》、《過春天》、《第一次離別》及《不止不休》等。其他主要剪接作品包括《再見瓦城》、《相愛相親》,而去年兩部作品——《南方車站的聚會》及《灼人秘密》,更雙雙入選康城影展。
由《你好,樹先生》到《天注定》 馬修與賈樟柯的開始
馬修早年修讀巴黎第三大學電影理論專業,當時與同學Damien Ounouri(《革命是可以被原諒的》導演)、李丹楓(聲音指導)製作了《小賈回家》,自此與名導賈樟柯結緣,由製作電影幕後花絮開始,逐漸涉足攝影及剪接;劇情以外,馬修亦為多部紀錄片操刀,包括《殤城》、《搖搖晃晃的人間》及《蜻蜓之眼》等。是次大師班將以他參與製作的電影為案例,講解剪接運作及劇情與紀錄片的不同面向,並分享其多種崗位於創作過程的化學作用。
馬修:謝謝New Cinema Collective邀請我舉行大師班,我非常期待電影節的其他活動,我尤其欣賞電影節的預告片!今天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職業生涯,這也是一個好的契機,因為2021年於我而言是很特別的一年──10年前我正好在剪接我的第一部劇情長片《你好,樹先生》(Hello Mr. Tree,2011)。
我是一個法國剪接師,我在巴黎第三大學(Université Paris III)主修電影理論,因為非常欣賞當時嶄露頭角的中國導演賈樟柯,2008年時跟同學丹米陽(Damien Ounouri)、李丹楓一同前往北京,拍攝賈導演的紀錄片《小賈回家》(Xiao Jia Going Home,2017)。拍攝完結後我們一起回到巴黎繼續學業,主修電影聲音的丹楓是中國的留學生,所以學成後他就回到中國,當上電影的聲音指導。當時我沒有工作,就到北京去學習中文。當時我希望成為一位拍攝指導(Director of Photography),丹楓與賈導的御用錄音師張陽老師就為我介紹了拍攝電影幕後花絮的工作,其中一部就是韓杰導演的《你好,樹先生、2011》。
韓杰當了賈樟柯的副導演很多年,所以賈導當上了《你好,樹先生》的監製。6個月後,賈導並不滿意《你》的初剪,韓杰知道我主修電影,跟他的電影喜好與口味也相近,所以問了我的意見。電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劇情,是主角樹先生的哥哥在他小時候已經死了,這對於王寶強如何演繹「樹」的角色,與整部電影的劇情發展都非常重要,可是導演版本(director’s cut)卻錯過了這事件出現的最佳時間點,觀眾很容易會摸不著頭腦。韓導聽過我的意見,便讓我試試在兩星期內重新剪接。當時拍攝已完成,也無法重新拍攝,所以為了讓整部電影的脈絡更完整,我提議加入旁白(VO,即Voice-over)。由於當時我的中文還是很差,所以拜托了當時的女朋友王思靜(現在的太太)幫忙翻譯,以下是我加入了旁白的3個片段:
從片段可見,加入旁白後,觀眾更容易理解主角的創傷與掙扎。這其實也並非電影的最終版本,只是一個新想法,但當賈導與韓導看到後,就豁然開朗──有時候,長時間的創作期會令你腦閉塞,而你只需要一些碰撞、一點火花,就可以走出困境。《你好,樹先生》是我參與的首部電影,也是我第一部親手剪接的電影,它對我尤其重要,也是我與賈導合作的開始。
兩年後,賈樟柯開始拍攝《天注定》(A Touch Of Sin,2013),他原本不想另外找剪接師,而是想副導代刀。但經歷了長達數月的緊密拍攝,副導太累了,希望回家過新年,賈導卻希望參選在五月舉行的康城影展,所以韓杰就推薦了不用過節,來自法國的我幫忙(笑)。開初賈導也怕因為文化背景的不同,我會難以明白他的作品,但初剪的兩星期我們合作無間,所以我最終成了《天注定》的剪接師。
賈樟柯是一個很有想法的導演,他在拍攝時早已決定好哪組鏡頭要放到電影的哪部份,所以剪接不能太天馬行空,要跟隨賈導的框架走;他也非常擅以長鏡頭拍攝,長鏡頭對於剪接師而言也有限制,因為每一幕可能只是由約2-4個長鏡頭組成,而你不能剪接長鏡的部分──畢竟你無法壓縮時間──所以剪接師的挑戰就在於如何選擇最好的鏡頭,同時與賈導保持良好又透明的溝通,令他的故事與想法能圓滿的呈現出來。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江湖兒女》(Ash Is Purest White,2018),滿滿的長鏡頭之中,我必須把握好電影時長,把故事枝節刪除;為電影佈下懸念,加強追看性之餘,也必須保留足夠線索,讓觀眾能看懂故事,並接收到電影想表達的訊息。
《天注定》共有4部份,以下片段是第一部份的終結與第二部份的開始,是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幕。大家可以看看在剪接上,我是如何將電影過渡到下一部份:
你可以看到第一幕,大海(姜武 飾)殺死礦主的一幕,長鏡頭之外,我只額外補充了一些零碎的鏡頭──如子彈飛出窗外、地下的血、車子與工廠的遠景,再接上大海染血的近鏡。這個處理,是因為賈導希望把電影做到帶點武俠片的感覺。
賈導的電影都很貼近現實,他也喜歡混合紀錄片與虛構情節。所以你看到第一、二部分中間的過渡,使用推軌鏡頭(Dolly Shot)捕捉三峽眾生相,是份外有紀實感的。而這一個鏡頭,其實也是《三峽好人》(Still Life,2006)的開場,你可以看到王寶強,也可以看到《三峽好人》的主角韓三明,配樂也是一樣來自林強(Lim Giong)的。
在《天注定》,賈導嘗試將暴力美學,像塔倫天奴、北野武般的,與紀錄片,甚至是現實揉合在一起,卻又一點都不突兀。這是我職業生涯其中一部最重要的電影,也許還是最棒的一部──因為這部片我贏得金馬獎「最佳剪輯」,為我開拓了剪接師路上很多的機會。也是這部片後,我專注成為一個剪接師,除了《卡夫卡的K》(K,2015)外已鮮有再充當攝影師了。
讓我再說詳細一點賈導如何將紀錄片元素揉合到劇情片中吧。《山河故人》(Mountains May Depart,2015)的故事分割為三個年代,包括1999年、2014年及2025年,為了塑造1999年的部分,賈導萌生了回頭查看舊影片的念頭──他在90年代末至00年代初期拍下了不少紀錄影像(documentary footage),尤其是他在拍攝短片《公共場所》(In Public,2001)時存下了很多。那是一個特別的年代,對中國發展而言,對賈導而言也是──畢竟那是他的青蔥歲月。賈導對這些「原汁原味」的舊影片愛不釋手,認為它們把那個年代的狀態、情感都清楚記錄了下來,而這是很難再度「翻拍」出來的──由是我們把約40分鐘的舊片段作為劇本的基礎,嘗試以情節連結起片段,再加入演員劇情的部分,將劇情和紀錄影像揉合起來。於我而言,《山河故人》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體驗──因為作為剪接師的我,在劇本「出生」之前,已經開始投入電影的創作了。
導演的長鏡頭 剪接師的大難題
賈樟柯是一個很有想法的導演,他在拍攝時早已決定好哪組鏡頭要放到電影的哪部份,所以剪接不能太天馬行空,要跟隨賈導的框架走;他也非常擅以長鏡頭拍攝,長鏡頭對於剪接師而言也有限制,因為每一幕可能只是由約2-4個長鏡頭組成,而你不能剪接長鏡的部分──畢竟你無法壓縮時間──所以剪接師的挑戰就在於如何選擇最好的鏡頭,同時與賈導保持良好又透明的溝通,令他的故事與想法能圓滿的呈現出來。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江湖兒女》(Ash Is Purest White,2018),滿滿的長鏡頭之中,我必須把握好電影時長,把故事枝節刪除;為電影佈下懸念,加強追看性之餘,也必須保留足夠線索,讓觀眾能看懂故事,並接收到電影想表達的訊息。
《天注定》共有4部份,以下片段是第一部份的終結與第二部份的開始,是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幕。大家可以看看在剪接上,我是如何將電影過渡到下一部份:
你可以看到第一幕,大海(姜武 飾)殺死礦主的一幕,長鏡頭之外,我只額外補充了一些零碎的鏡頭──如子彈飛出窗外、地下的血、車子與工廠的遠景,再接上大海染血的近鏡。這個處理,是因為賈導希望把電影做到帶點武俠片的感覺。
賈導的電影都很貼近現實,他也喜歡混合紀錄片與虛構情節。所以你看到第一、二部分中間的過渡,使用推軌鏡頭(Dolly Shot)捕捉三峽眾生相,是份外有紀實感的。而這一個鏡頭,其實也是《三峽好人》(Still Life,2006)的開場,你可以看到王寶強,也可以看到《三峽好人》的主角韓三明,配樂也是一樣來自林強(Lim Giong)的。
在《天注定》,賈導嘗試將暴力美學,像塔倫天奴、北野武般的,與紀錄片,甚至是現實揉合在一起,卻又一點都不突兀。這是我職業生涯其中一部最重要的電影,也許還是最棒的一部──因為這部片我贏得金馬獎「最佳剪輯」,為我開拓了剪接師路上很多的機會。也是這部片後,我專注成為一個剪接師,除了《卡夫卡的K》(K,2015)外已鮮有再充當攝影師了。
在未有劇本前 啟動剪接 《山河故人》的全新嘗試
讓我再說詳細一點賈導如何將紀錄片元素揉合到劇情片中吧。《山河故人》(Mountains May Depart,2015)的故事分割為三個年代,包括1999年、2014年及2025年,為了塑造1999年的部分,賈導萌生了回頭查看舊影片的念頭──他在90年代末至00年代初期拍下了不少紀錄影像(documentary footage),尤其是他在拍攝短片《公共場所》(In Public,2001)時存下了很多。那是一個特別的年代,對中國發展而言,對賈導而言也是──畢竟那是他的青蔥歲月。賈導對這些「原汁原味」的舊影片愛不釋手,認為它們把那個年代的狀態、情感都清楚記錄了下來,而這是很難再度「翻拍」出來的──由是我們把約40分鐘的舊片段作為劇本的基礎,嘗試以情節連結起片段,再加入演員劇情的部分,將劇情和紀錄影像揉合起來。於我而言,《山河故人》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體驗──因為作為剪接師的我,在劇本「出生」之前,已經開始投入電影的創作了。
以下是《山河故人》的片段:
《山河故人》的這場戲十分複雜,讓我分成幾個段落,解釋背後的拍攝和剪接手法。
兩位主角的畫面使用ALEXA拍攝,是劇情片常見的鏡頭。接著的人潮和慶祝畫面處理很特殊,我們先於電視上播放賈導在90年代拍下的紀錄影像,然後再用拆走了鏡片的攝影機拍攝電視上的畫面,構成一種怪異的視覺效果。我們使用紀錄影像並不旨在紀實,而是希望能充分地呈現懷舊(nostalgia)的感覺。富有質感的影像加上音樂,令我們回憶起90年代的中國,那個不再存在的模樣。拍攝團隊再用同一部攝影機拍攝演員的部分,透過美術設計和道具,重塑紀錄影像中出現過的顔色和雨傘,加插在紀錄影像之間,讓我們能無暇融合敘事,有演員的畫面和從前拍下的素材。
接下來趙濤表演的畫面我們用了ALEXA拍攝,不過我不太滿意,因為畫面太高清了,不太符合這幾場戲的感覺。但正如法國著名影評家巴贊(André Bazin)所説,電影剪接的首要規則就是要有觀眾和演員的視覺,所以除了趙濤在台上看著觀眾的畫面,我們也需要保留從觀眾席後方拍攝觀眾和趙濤的遠景鏡頭。我們必須尊重這些規則,看電影的觀眾才會相信電影中的人是同一時間,在同一個空間存在。
緊接的幾個畫面由紀錄影像和我們拍攝的片段交織而成。人山人海的群眾畫面,就算找上千個臨時演員也不太可能拍到,所以我們選擇用真實的錄像。這幾場戲很成功地將紀錄影像與劇情片的敘事和演員的演出融合。
短片的經驗 聲音的重要性
我也剪接過一部法國短片《Ceremony》(2016)。在短片開始時,我們看到一位法國老人在巴黎某處的酒店房裏等候,雖不清楚事情的始末,但我們知道這老人曾經在東南亞國家打仗,而他在戰場上的經歷,對他造成巨大的心理創傷。
在酒店房的他準備打電話給他的前妻,然後請一名妓女,並在她的身體上作畫,待一切結束後,他便計劃服藥自殺。這個短片雖是關於戰後創傷,但沒有拍攝任何打仗場面。在收到導演和攝影師的素材後,我覺得為了讓觀眾理解老人的角色和行為,一定要找方法表達他在戰爭中目睹的事,於是我在網上找了一些關於克什米爾衝突(Kashmir Conflict)的紀錄影像,再剪輯了影像和聲音。
我在短片開首加入衝突中平民傷亡的照片和錄像,透過這些暴烈的畫面,觀眾就能想像老人在想什麼。我在《革命是可以被原諒的》(Fidaï,2012)中對紀錄影像也有相似的處理,但兩者的聲音設計卻完全不同。在《Ceremony》,我堆叠了很多段不同的聲音,讓觀眾能真正感受到充斥著老人腦海裏的聲音和畫面。
《蜻蜓之眼》沒演員沒攝影師 「剪接」成為主角
我在其他電影也有用到這種聲音設計的技巧,包括我電影生涯中第二重要的作品──中國著名藝術家徐冰執導的《蜻蜓之眼》(Dragonfly Eyes,2017)。這部電影由多達11,000小時的閉路電視錄像剪接而成,包含中國多個不同地方的錄像。徐冰希望以真實的錄像説故事,築構一部沒有演員,沒有攝影師的劇情片。這部電影對我意義非常重大,它十分具挑戰性,是我參與過難度最高的電影,我大概花了一年時間剪接。
接下來,我會播放《蜻蜓之眼》的預告片,然後分享我在過程中學到的技巧和它對我的重要性。
這個預告片由我剪接,亦是我少數覺得滿意的預告片。《蜻蜓之眼》的對白都是在剪接期間,根據影像而寫,自此我剪接劇情片時也會沿用這個技巧。有時到了剪接期間,才會發現某部分的故事説得不清楚,我們便會按照演員的口型重寫對白,透過同步對白錄音(automated dialogue replacement, ADR)取替本來的對白。
參與《蜻蜓之眼》也讓我學到如何對拍攝素材作質感上的處理。我們透過平面設計(graphic design),在錄像中加上圍著人和事物的紅色、綠色方框,文字和數字,令電影敘事更完整。《蜻蜓之眼》對我來説是革命性(revolutionary)的電影。我一直參與的電影大多視剪接為輔助影像的工具,剪接師的角色越隱形越好,我們的工作就是突出故事、演員和美麗的畫面。但像在《蜻蜓之眼》的預告片中,我們除了看到真實的錄像,也能明顯地感受到剪接的存在。
接下來我們一起看看刁亦男導演的《南方車站的聚會》(The Wild Goose Lake,2019)。雖然它是近一兩年的作品,而我這樣説可能有些言之過早,但我認為它是我事業上第二個轉捩點。《南方車站的聚會》是一部具强烈風格的類型電影(genre film),劇情很複雜,鏡頭也比一般電影多。
賈樟柯、趙德胤等導演較多使用長鏡頭,觀眾有更長時間認識空間裏的物件,不會容易覺得迷失。但零碎的鏡頭,令空間的呈現變得更困難和複雜,剪接師便擔起解決問題的責任。我現在會分享電影接近結尾的片段,所以先跟還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道歉,但我相信不會劇透太多故事的内容。
這幾場戲的剪接和呈現的空間極為複雜。我們首先用同步對白錄音(automated dialogue replacement, ADR),簡單地修正對白,令故事更清晰。在畫面中,我們看到女主角把手上的302號房鎖匙交給男主角,叫他15分鐘後上去,下一個鏡頭我們看到女主角行樓梯。在拍攝期間,當她走到一半,飾演警察的演員也走進同一條樓梯,更巧合地同時抵達樓梯的頂端。但劇本寫的是警察跟蹤女主角,所以他們同時在樓梯出現並不合理。我在剪接時將樓梯的畫面分成兩半,較先出現的是女主角獨自行樓梯的幾秒。我們也用特效在樓梯旁邊加上「台球室」的霓虹招牌,好讓在之後警察行樓梯的鏡頭,觀眾能立刻認出是同一個空間。
接著我們看到警察,他們大概知道男女主角的藏身之處,正要往那裏出發。但因為他們穿著便衣,觀眾未必知道他們是警察,或會以為他們是黑社會,所以我在兩個行樓梯的片段之間加插了他們的對話。
下一個畫面是警察走上樓梯,走進302號房正樓下的房間。雖然我們知道男主角在旅館,但不清楚他在哪一層,所以我們在他的後方加了一件正在墜落的垃圾,以這件物件貫穿三個畫面。如此,我們就可以清晰地理解電影中的空間和角色所在的位置:男主角在三樓,警察在二樓,而垃圾最後跌在地面。梳理好空間的脈絡後,我們便會知道警察樓上傳來的聲音,很有可能來自302號房。我和刁亦男導演就是這樣處理這個複雜的段落。
導演與剪接師如情侶 保持開放 建立信任
對不起,我有點超時,我希望可以分享和年輕及富有經驗的導演合作的經驗,不過同時亦很想能詳細地解構每場戲的處理。
有經驗的導演更熟悉剪接的規則和電影製作的整個過程,所以跟他們合作通常比較簡單、直接和快。但也不是每次都這麼順利,當你做了一些他們不喜歡的事,有些導演就會開始對你失去信任,之後要花很長時間才能重新建立關係。導演與剪接師的關係就像情侶,要保持開放的溝通,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而很多新導演在拍首部長片時,普遍對剪接較為保守,不太容易接受新的想法。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構思整部電影和寫劇本,怕任何改動會影響電影的原創性,改變整個作品,所以與新導演合作,需要時間互相認識與磨合。
其實任何劇本一開始總會有問題,如緊拙的資金、演員的表現、拍攝日程等因素,都會在拍攝期間衍生新的問題,所以我們基本上不可能完全按照原訂劇本剪接。有些新導演覺得只要寫完劇本,排好拍攝次序,就不會有任何問題,但在我過去的經驗,事情從來也不會這麽簡單。
我在《卡夫卡的K》和《革命是可以被原諒的》身兼攝影師和剪接師。因為我有份參與拍攝的工作,在剪接時我發現自己失去了剪接師應有的特質,我不能像平時一樣,以第一位觀眾(first audience)的視覺看拍攝好的素材。
新導演們常常會誤以為觀眾跟他們一樣,也會察覺和明白他們用心安排的每個小細節,但觀眾其實不會接收到畫面上的一切。在看電影時,每個人都會聯想起不同的事情,電影的某個情節可能令你想起一些往事或經歷,你自然就不會那麽專注地看銀幕上發生的事。所以在剪接過程中,每位導演都要嘗試忘記自己導演的身份,忘記努力創作的過程,以觀眾的視覺看待自己拍攝的影像,我覺得這就是每個導演,尤其是新導演最大的挑戰。
討論會中的問答環節
1/ 從劇本、拍攝到剪接,你是如何嘗試理解導演的敘事(narrative)?
馬修:我大部分製作的電影都是華語電影,我的中文程度有限,簡單的訊息、日常生活都可以明白,但還未達到可以看懂整份劇本的程度。所以,如果沒有英文劇本的話,我通常就會跳過讀劇本這一部分。我的工作伙伴是來自台灣的剪接師,她會大概告訴我故事內容。我通常喜歡在拍攝的第一天就開始剪接,在拍攝過程中,我會有時間去消化、剪接電影的每一幕,同時決定每組鏡頭的時序;到拍攝完結時,我大概已掌握到整部電影的故事內容了。也因為我不看劇本的原因,我更可於剪接時秉持「第一觀眾」的身份,從觀眾的角度去慢慢拆解故事情節與電影角色。去到剪接終於完成,我也就豁然開朗,全然理解整部電影了。這也是我喜歡當剪接師的原因。
2/《蜻蜓之眼》由超過11,000小時的監控畫面剪接而成,面對如此龐大的訊息量,你是如何將錄影片段剪接成一個完整故事呢?你又是如何與導演合作的呢?
馬修:這個問題,我想我可以回答5個小時(笑)。我投入《蜻蜓之眼》時,製作團隊其實已完成劇本創作,那是一個劇情片的劇本。他們在下載監控畫面時,發現有很多例如寺廟、街道、工廠等片段,所以就把這些場景寫到劇本中。電影裡沒有演員,我需要從10,000多小時的監控畫面中尋找與劇本中寫好的場景、主角甚至是對白都符合的鏡頭。在芸芸眾生之中,還要考慮主要角色的一致性,電影中一男一女主角,他們的呈現方式主要是聲音上的,但在畫面上也要讓觀眾能幻想到片段裡的人都是同一人,所以我們在監控畫面中還要找尋相近的輪廓、身材的人來配合。
我、導演徐冰與編劇翟永明合作非常緊密。例如當我找到一個合適的錄像時,我會先跟導演的助手去按照「演員」的口型重寫對白與錄音,再試試新對白能否對上畫面,通常這都需要反覆試驗才能成功;然後我會將片段給導演與編劇看看,他們又會再反覆寫新的對白。
3/ 如果剪接師需要在後期加入旁白與改動劇本,那是否應該從拍攝時就嘗試做好呢?
馬修:我覺得從開始就達到完美是不可能的。即使像《天注定》,在看拍攝的錄像時我認為完成度已經很高了,也知道這一定會是一部好電影,但我們在剪接階段還是修改了很多部份,刪走了不必要的,也重拍了一些鏡頭。在拍攝時,你一定要全力而赴,但縱使如此,能拍出完美鏡頭的機率還是很小。這也是為何剪接是如此重要的原因──那是一個讓我們重新思考、碰撞新想法的創作過程。
當然有一些人會批評加入旁白的做法,但就如金棕櫚導演泰倫斯馬力(Terrence Malick),大家都認為他的電影是充滿藝術性的大師級作品,他其實也是旁白的愛好者,如他的早期電影《窮山惡水》(Badlands,1973)、《天堂的日子》(Days of Heaven,1978)、狂林戰曲(The Thin Red Line,1998),與為人熟悉的《美麗新世界》(The New World,2005)、《生命樹》(Tree of life,2011)等,也加入大量旁白,那是他的藝術,他的表達手法。
如果加入旁白只是單單為了資訊性的考慮,那的確不夠有趣味性。你必須把旁白與角色連繫起來,也讓它成為電影風格與美學的一部份,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作為剪接師的職業生涯中,也只有《你好,樹先生》能成功加入旁白而已。
4/ 你在看錄像時,會抄筆記嗎?你是如何處理海量的素材呢?
馬修:我不會做筆記。我喜歡一邊拍攝一邊開始剪接,通常在每一天拍攝後我會選取「過關」的鏡頭,先作一個簡單的剪接,讓自己先理解那一幕的情節,也看看邏輯對不對;到後期我已有一個大概的剪接藍圖,我才會重新看一次所有鏡頭與錄像,找一下有沒有更好的選擇。我不會在一開始就看所有的鏡頭,例如有時賈導同一組鏡頭可以拍30次──當你重覆又重覆地看著類似的畫面,你會失去最初畫面帶給你的震撼與情感。剪接是一個不斷重覆的過程──剪片、突破新想法、與導演接洽、重看片段……我必須為自己保留一些新鮮感。
5/ 剪接師在剪接的過程中,是否必須聽從導演與監製的決定?
馬修:拍電影是一個多方合作的創作過程,我不認為剪接師與導演及監製在立場上是相對的。很多時候,其實不論是導演、監製,甚至是投資方、影評人、朋友,甚至是審查制度,他們都各有一些不同的考量,當他們給你一些建議時,盡量以開放的心接受,其實很多時候,這些都是一些新的想法,即管放手一試吧!如果試了之後不喜歡,大不了便用回原本的方案,不會浪費。當你試得越多,你會發現自己不喜歡的、不想要的,那你與理想作品的距離便會越來越接近了。
被批評和被「迫」改動作品,或許是不少年輕導演的掙扎。不要固執地覺得因為接納他人的建議,那作品就不完美、不夠理想、不夠「你」了。這些建議與新想法,或許會進化成與別不同的表達方法,甚至最後會發現這才是自己想要的。
儘管一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