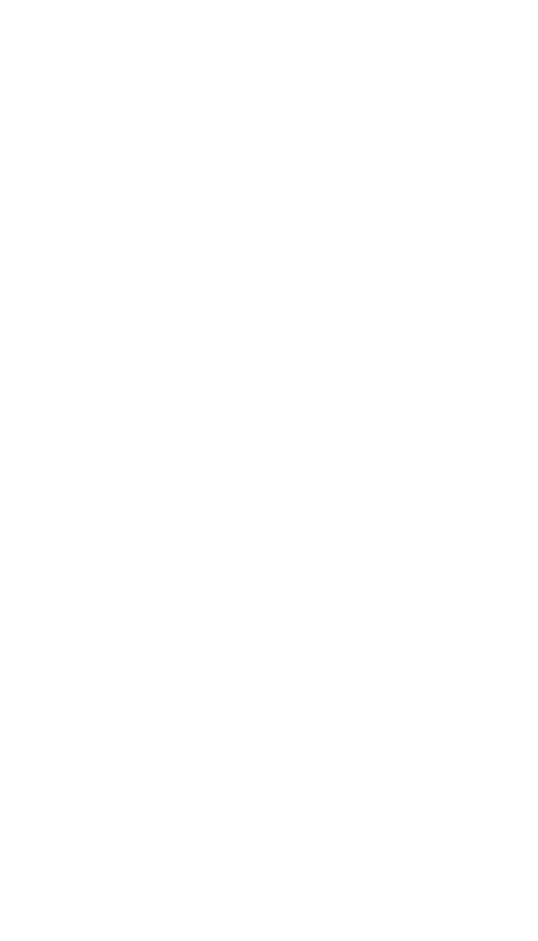華語新銳電影的市場與定位
時間:2020年2月27日 (六) 20:00 – 21:30
地點:Zoom
主持:楊寶文(香港監製、《世外》編劇)
與談:吳蕙君(台灣 光在影像創辦人,曾在寰亞電影及安樂影片從事發行工作)
曹柳鶯(台灣 視幻文化創辦人,電影自媒體深焦DeepFocus聯合創始人)
郭斯恒(台灣 日映影像創辦人)
文字紀錄:《誌》
文字校對:何梓埼
近年香港獨立電影漸受國際關注,年輕影人亦嘗試於創作及資源上另闢蹊徑,在此起步階段,國際發行擔當著什麼角色,以助本地作品走得更遠?討論會將聚集三間發行公司負責人──光在影像、日映影像及視幻文化,探討華語電影於國際市場上的定位,及如何協助新銳影人與作品建立口碑;同時回應疫情下的機遇。


光在影像
吳蕙君
吳蕙君,美國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碩士。曾於杜琪峰導演的銀河映像參與製片工作,隨後任職香港寰亞電影的國際發行部門及名製片人江志強先生的香港安樂影片公司擔任國際發行部總監。 從事電影國際行銷工作多年,並發行逾百部華語電影。 於2013年創立光在影像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於推廣與行銷多元類型的華語電影佳作;同時亦擔任台北發行工作室的特別顧問、澳門國際影展曁頒獎典禮的電影市場總監,以及台北電影節南特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講師;並於台灣各大電影相關機構擔任產業諮詢委員及顧問。

日映影像
郭斯恒
郭斯恒,大馬華裔,目前定居台灣。監製、國際發行,日映影像創辦人。監製作品包括《阿尼》(2016)入圍康城國際影評人週、《你的電影我的生活》(2018)獲選北京國際短片電影節最佳短片。

視幻文化
曹柳鶯
曹柳鶯,電影自媒體深焦DeepFocus聯合創始人,擁有豐富電影節經驗,連續七年代表多家華語媒體赴戛納、柏林、威尼斯、釜山等海外電影節進行報導,發表影評、電影創作者訪談超過500餘篇。同時從事製片及海外發行工作,參與項目包括《柔情史》、《星溪的三次奇遇》等。 2018年出品影片《漫遊》入圍釜山電影節新浪潮競賽、柏林電影節、香港國際電影節華語競賽等數十個海內外電影節。

主持
楊寶文
楊寶文,監製及編寫動畫《世外》(2019),獲DigiCon6 Asia大賞全場大獎、ifva動畫組金獎等。2020年《世外》動畫電影計劃獲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劇情片大獎」。 其他監製電影包括《女皇撞到正》(2018)、《非分熟女》(2019),入選烏甸尼、大阪及荷蘭等亞洲影展;編寫真人動畫電影劇本《肩上蝶》(2011),入圍上海國際影展。
國際發行的角色 讓電影被看見
主持楊寶文:我相信今天很多來到這個網上專題討論會的朋友,大部分都不是太清楚「國際發行」、「導演」,還有「監製」這三個角色的合作是怎樣的,作為一個「國際發行」,你們通常從那一個階段參與製作呢?
吳蕙君:時間點來說,因為台北很小,在這個「國際發行」的範疇久了,大家都會互相認識,然後我也是很積極參與很多業界會議去搜集資料的人,我覺得兩個面向都有,包括是一些有趣的案子,我會主動去詢問,另外就是製作方主動來找我。
如果我不是太認識那個製作方的話,我會比較想在在快進入後製的情況下加入,因為這樣我可以看的東西會比較多,比較容易評估。但如果是我很熟悉的創作人,例如是一直有合作的伙伴,通常在啟動計劃,甚至在寫劇本時,我已經參與。
曹柳鶯:我們是從一個自媒體「深焦 DeepFocus」起家的,自媒體的工作跟海外發行其實是有一段距離。
我們在初期接到的案子是張大磊導演的《八月》(The Summer Is Gone,2016),以及梅峰導演的《不成問題的問題》(Mr. No Problem,2016),當時這兩齣電影已經入圍東京電影節。源於我們本身媒體人的身份,和導演、製作商比較相熟,所以他們不介意向我拋出一個困惑:如何在電影節中推廣自己的作品?
由此可見,部分內地的製片方對於海外電影節沒有這麼熟悉,所以在他們的眼中,這些繁瑣的公關工作是非常耗費精力,然後我們團隊獲邀在東京電影節中,幫忙他們去完成與電影節溝通與交際的工作,慢慢在不同電影的活動中,接觸到更多內地的製片方,發現他們對於海外的這個部分真的不太暸解,所以我們就從這個切口入手,算是一個自媒體人到電影從業者的轉型。
因此,對於不太熟悉的製片方來說,我們都是在後期階段參與,以便有更多的影像可以參考,對電影的質量有一個準確的判斷,還有對它的海外前景有所預估。
在這個行業兩三年後,有些導演會向我們推薦一些作品,以竹原青導演《星溪的三次奇遇》為例,因為是梅峰老師監製的,我們有了之前《不成問題的問題》的合作經驗,所以在更早期的時間,甚至在還沒開拍時已經介入,在國際的層面上為他們提供一些意見。不同階段的參與都會發生,要看影片的具體情況。
郭斯恒:我是從製片入行,當時第一齣以這個身份參與是電影《阿尼》(Arnie,2016),這齣片後來入圍康城國際影評人週,那時候,我和團體帶著這個作品,像帶著一個初生嬰兒(Newborn baby)去了很多影展,然後甚麼都不懂。
關於影展的事情全部都是製片人,也就是我自己在做,包括宣傳、發行等等。這次經驗令我思考了「國際發行」這件事,然後在2018年創立了「日映影像」這一家公司,初期最大的困難是找片源,原因時大家不清楚我們是誰,不暸解我們的公司。所以我會很主動的去看看電影圈裏,有那些導演正在拍片,有那些預告片我看過後覺得意念很新,很特殊的,我就會邀約,看看有沒有合作的空間。
另外,我同時也在做短片的製片,主要留意那一些導演是有潛力的,我都會先跟他們合作,奠定了根基和培養了默契後,接下來他們的第一齣,或是第二齣長片,我就會很容易可以拿下他們的國際發行。
簡單來說,我是從短片發掘根源,慢慢建立強大的聯繫(Connection)。
在國際市場 短片像職場上一張名片
主持楊寶文:特別是在香港,很多新銳導演的入行以短片為先,以你們三位的經驗,短片能賣錢嗎?
郭斯恒:老實說很難,短片比較像是一張導演的名片,就是讓世界上的演員、監製、出品人、老闆認識到你的一張名片。我覺得以這個想法去做短片會比較好,當然有時候會有一些錢回來,但絕對不會是作者的第一考量。
主持楊寶文:我相信有很多電影工作者在發展自己的電影項目時,會有很多的想像,例如我的作品去東京電影節,還是康城影展好呢?你們三位去了很多的電影節,有很多經驗,能分享一下歐美和亞洲的電影節有甚麼分別呢?
曹柳鶯:與其說分別,不如說每一個電影節在選片上都會有不同風格。
以歐洲和北美為例,兩者更是完全不一樣的體系,北美的電影節對表現外族文化、非英語影片的接受程度和包容度是沒有歐洲的那麼開放、好奇。因為電影節本身是一個大眾文化活動,不同的電影節有不同的特色,這跟它們本地的電影文化和觀眾的觀影習慣是緊密相連的。
而華語影片的氣質大多數是偏東方,或者是承載著很多本土(Local)的東西,所以我的經驗是把華語影片推去亞洲、歐洲的電影節是比較順利,但走北美的電影節相對上是有挑戰性的,因為北美的評審們對劇情上節奏的快慢有一套截然不同的標準和口味。
吳蕙君:是的,一些華語電影去了亞洲不同的電影節後,對電影在本地的發行、反饋、宣傳上是加分的,例如釜山國際電影節、東京國際電影節等等,特別是釜山是專門有為「新導演」而設的,也幫助到很多新銳的創作人。

華語地區與非華語觀眾口味不同
主持楊寶文:華語電影在華語地區和非華語地區銷售方面,是不是有很明顯的區別?
郭斯恒:林龍吟導演首部劇情長片《蚵豐村》(Ohong Village,2019)在華語地區的銷售反而比較難,因為林導演是在歐洲學藝術回來的,他整個電影語言是偏歐洲一點,所以他的作品反而在歐洲電視台、外國串流平台和電影節有比較大的詢問度。
曹柳鶯:我跟師恆的想法有點像:即便是華語電影,並不代表在華語地區的發行是一帆風順的,我覺得可以歸咎於在華語地區上的觀眾覺得電影還是娛樂,所以他們對藝術片、作者電影、敍事流暢度會有一個期望,希望是快節奏、輕鬆一點的,所以我們公司接到的影片,其實在歐洲發行會比華語地區更好一些,例如在法國,我們也有電影可以在當地電影院上映,但反觀在華語地區院線發行是難上加難。
吳蕙君:我經手的華語電影類型比較廣,由中港兩地的合拍大片到台灣的那種將近四小時的黑白藝術片也做過。
我想補充的是,一些華語的商業片是完全有機會做到同步預售,以及同步戲院上映的,但數量真的不多,像我們公司經手的有《無雙》(Project Gutenberg,2018)、《中國機長》(The Captain,2019),以台灣片來說,《痞子英雄》(Black & White,2019)也有預售的,大約發生在2014年左右。
除了《日曜日式散步者》(Le Moulin,2015)比較特別以外,因為這是一部四小時的黑白紀錄片,上院線比較難,所以才會走影展巡迴。有一些比較商業的的華語藝術電影,例如《范保德》(Father to Son,2018)、《百日告別》(Zinnia Flower,2015)等等,一拉到國際發行的平台上,在賣家的角度來看,它們是一樣的。
新導演需多做功課 暸解業界與時並進
主持楊寶文:如果年輕的電影創作者想知道多一些行內訊息、市場動態,在座的三位,會推薦他們看甚麼平台嗎?
吳蕙君:無論是做發行、製作,以至任何崗位,現在網絡普及,國外關於電影業界的新聞是很容易得到的,而且還有很多免費頻道可以訂閱,即便是Facebook的一些專頁,也有很多資訊提供,但也有一些平台是專給業界登記,例如Cinando,通常這些平台的操作是需要持續地出席各個市場展,保持活躍,就可以保留帳戶。
郭斯恒:在年輕的時候,因為我很好奇市場展到底是長甚麼樣子?為甚麼印度電影是長這樣子?德國電影又是怎樣呢?所以在我剛開始想要理解影展和國際發行時,我是親自買機票去不同的市場展和影展。
我覺得只要你親自去一次,踏入這些場地,其實對很多東西會有所感受。
剛剛吳老師提到的一些線上App,我覺得那是作為一個電影創作者的基本功課,就是要知道最近國際影壇在發生甚麼事情,在關注甚麼樣的電影、題材等等。
曹柳鶯:在這個年代,獲取資訊的門檻是比較低的,我覺得你一旦建立了有關電影的聯繫,那怕只是臉書的一些專頁或群組,其實你每天瀏覽他們的資訊、提供的各種機會,已經多到看不過來了。
但是背後可能有一個更重要的知識是,不管是製片人想把自己的影片推到國際舞台,還是國際發行商想把手頭上的電影找賣家(Buyer),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大量看片。
「大量看片」的意思不僅僅是看那些需要你去推廣的電影,或者是案子,還有各個影展中不同的作品,作為一個影迷,你要真正暸解到每一個影展的選片人的口味,他們選出來的是那些華語片,你多多少少會有一點感覺的。因為這些都是很主觀的個人審美和愛好判斷。
至於你的作品是走影展也好,找賣家也好,要以成功的範例作為參考,以《路邊野餐》(Kaili Blues,2015)為例,你除了留意是那個發行商幫他們做地區發行,就算你把這些發行商都列了出來,你也得知道《路邊野餐》是一個甚麼樣的電影,跟你的電影有沒有可比性,所以我覺得大量的觀影是一個非常必要的功課,包括你的審美和口味也要跟電影節與時俱進。
疫情下「國際發行」新交流方法
主持楊寶文:總的來說,年輕的電影人要保持敏感性,留意業界的發展。話說回來,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影展都改成線上放映,這對「國際發行」的工作有影響嗎?
吳蕙君:沒有疫情時,我一個月起碼飛一次,包括市場展、電影節、宣傳的行程,這樣的生活接近20年了,我的人生用了這個方式過了很長時間,去年突然不用飛了,我真的覺得舒服了很多。
停下來後,我知道這樣講,可能有些人覺得不太高興,但我覺得這個行業好像真的不需要這麼多市場展,當然面對面的交流是很重要,但數量有點太多。它的數量有點超過了實際上的需求,很多事情可以像我們這樣線上開會去完成。
至於,影片銷售操作的方面,因為有很多製片方是不希望把影片放在市場展,他們擔心展內的安全機制。而且現在很多影展轉了線上,製片方對市場展的參與度就更不高了,加上,線上放映這個模式已經改變了很多觀眾的觀影習慣。作為國際銷售,我也在觀察中,到底線上放映這件事情有沒有幫助,有助影片在各方面加分。
郭斯恒:的確飛行時間變少,在疫情初期,我一度擔心自己的工作會不會被影響,畢竟我們是經常跑影展的人。但後來發現很多事情都能夠在線上解決,成本也降低,然後人的體力、精力也保留了很多,有更多的時間思考電影往那邊走,可以跟導演談的時間也多了,甚至在電影發生之前,已經可以介入。
因此,國際發行的整體工作不會因為疫情有很大的改變,但就觸發了很多的思考。
曹柳鶯:無論是時間、金錢和體力上的成本的確下降了很多,我覺得包括一些地區發行上的選片人,也不用跑了,他們的精力也多出了很多,有時間來跟你聊天。
在疫情之下,大家對於交流是有一定的慾望。
因此,他們更願意來跟你交流了。平時的話,大家都很忙,選片人手握大權,容易讓人覺得他們高高在上的,但在疫情下,大家偏向圍爐取暖,增進感情,這是一年來,工作上明顯的一個轉變和體會。
關於線上放映,本身這個方式也存在版權的問題,即使那個線上平台做得再謹慎,觀眾隨意拿個手機錄影,資料外洩的風險還是存在。反正就是沒有完全打消製片方的顧慮,他們會考慮很久要不要參與這些線上放映的影展、要給甚麼發行商看,兩邊的工作都要顧,有點吃力,但我是完全能理解製片方的憂慮。
對於小電影來說,他們有國內發行上院線的計劃,也有在國內賣VOD(Video On Demand,隨選視訊,包括線上串流平台點播等)版權的計劃,電影一旦外洩,他們可能連唯一的收入渠道都沒有,所以一定是非常謹慎的,我的角色是盡量去做中間的平衡工作。
另外就是回到電影節的宣傳,一般電影節本身會製造很多話題(Buzz),如果電影是首映的話,大家都會集中在談這部電影,其實很容易就會引起發行商的關注,也許他們本身沒有在關注,卻巧妙、間接地促成一些銷售的機會。
但線上放映後,在各種平台發佈資源很分散,可能這個話題就沒有那麼強了,這個時候發行商就更不可能關注到你的電影,需要你主動去推。
視覺元素最吸晴 影展履歷如同個人履歷
主持楊寶文:香港的電影教育只談創作,很少提到發行、影展的問題,你們有甚麼看法嗎?短片該怎樣走影展,策略是什麼?
郭斯恒:我一年大概看300到350套短片,假如你有一部短片,我會先看,然後跟你說說我的感受,再告訴你(上院線的)機率高不高,而它會是哪些影展喜歡,你可以自己去投影展,也可以找像我們這樣的國際發行公司幫你,這是兩條路。但首先必須知道電影的定位在那裏。
主持楊寶文:短片也好,長片也好,創作人要把影展最關注的故事梗概、大綱(Logline、Synopsis)寫好,因為一個影展中有太多電影了,首先第一印象是文字必須寫好,吸引選片人去看。
郭斯恒:我也好奇,想問問兩位,你們覺得把電影交給賣家的時候,最先吸引他們眼球的是甚麼呢?
曹柳鶯:我自己的經驗是,如果你的電影已經走過影展了,那影展的履歷是重要的,說白了大家比較功利,這是一個最明確的篩選方法,影展的履歷跟一個人的履歷是一樣,如果你去過影展,你的影展履歷當然是愈高愈好。
如果是一個比較初期的電影,例如初剪完成後,在一個預售(Pre-sales)的階段,或你剛剛開始進行影展工作,同步想開展電影節的銷售,我覺得視覺上的物料會比文字上的更有說服力,因為文字很難呈現一個創作者的影像風格。
一個故事梗概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拍法,如果你是一個新導演,賣家也沒有看過你以前的作品,視覺物料,例如預告片,就可以讓他們直接看到你的作品風格。
有時候,我覺得有些創作人待在一個作品太久了,比較難跳出來看自己的作品,表達慾望也比較強烈。有些電影你看完了覺得甚麼也沒說,但是導演還是可以跟你說一堆東西。因此,銷售公司、推廣部門在這裏要扮演一個角色:要從導演給你的東西中,從外部的角色,一個外國視覺、市場、觀眾、影展的角度把導演給你的東西中進行提煉。
甚至在海外影展中,國外觀眾關注的點,也不一定和本地觀眾一樣,這也是我們需要給製片方的意見。
吳蕙君:是的,視覺素材是很重要的一環,我經常會在國外的市場展擺攤位,一個好的視覺素材(Artwork),例如海報、預告片等等,真的會讓賣家停下來,多問兩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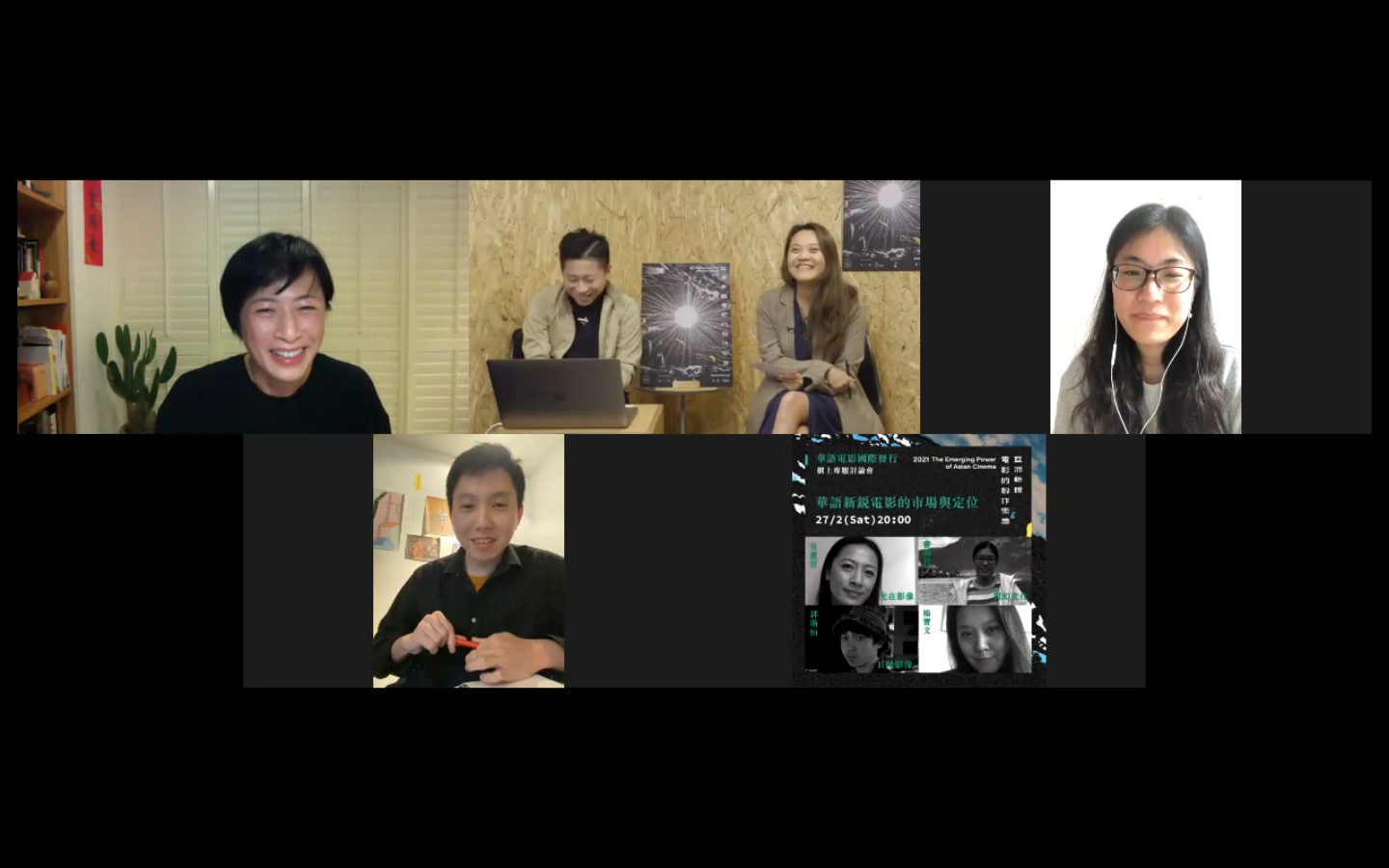
不摒棄線上平台 不賠錢能繼續拍 至為重要
主持楊寶文:現在有很多線上串流的平台,例如iTunes,觀眾付費就可以即時觀看,對於作品曝光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作為「國際發行」,對於這些平台,你們有甚麼建議嗎?會影響電影的版權,或是之後參與影展的機會嗎?
郭斯恒:我這邊的經驗,導演通常要求先把影展走完,再考慮線上的放映,而我的公司發行的作品以影展為主。
曹柳鶯:我也不太建議導演一開始就把作品放在線上,長片肯定是以影展和銷售為先。
但短片來說,其銷售機率比較低,如果在影展上走得差不多時,可以考慮做,這個方法也是歐洲相對比較流行的,有很多銷售公司會把手上比較舊的作品,在版權買賣、影展周期結束後,放到線上平台上付費點播,作為一個作品的結尾。
吳蕙君:最近我有一個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年,我參與了許承傑導演的《孤味》(Little Big Women,2020)發行,在影片後製還沒有真正完成的階段,我已經看完了,就確定要接這個案子,啟動銷售的工作。
在這個期間,我接觸了很多賣家,當中包括一家非常知名、家傳戶曉的線上串流平台,我們很快談成了一個很好的價錢,一個就算是分開來賣也沒辦法有這麼多的價錢,所以我很自然地就回頭跟製片方匯報,嘗試達到一個協議。大家也知道把影片放上了一個這麼大的線上串流平台後,是限制很多後續的東西,包括影展的發展。
但作為一個「國際發行」的角色,就是盡量替製片方爭取最大利益,當然這要看你談的時間落在那裏,如果說影片已經上映了,台灣也發行了以後,這是另外一個談法。
只是在這個案例上,所有東西都發生在很前期的階段,所以很多東西是可以爭取回來的,就好像在沒有跟這個線上平台談好之前,我已經跟香港國際電影節談定了開幕片的決定,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影展延後,因此我又有了機會談東京國際電影節和釜山國際電影節,這個是一個不尋常的狀態,但為這個作品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
因此,回歸到電影的本身,要看看回報的壓力有多大,要做取捨。
總而言之,我認為網上串流平台也不是要摒棄,我真的覺得很多電影要在戲院被看見,對電影工作者來說,或是大家集合出來的創作,這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只是說,很多時候,太多電影未必做到這樣,尤其在戲院發行成本這麼高的情況下,所以戲院跟線上平台是一個取捨,我覺得做任何電影就是不要賠錢,電影工作者們就可以一直拍下去,創作能繼續是最重要的。
線上平台的實際操作
主持楊寶文:談到這個線上串流平台的經驗,有觀眾想問,在你們談版權費時,到底是甚麼時候決定要跟平台設定一個最低收費(Minimum charge),還是訂戶付款(Pay by subscriber)呢?
郭斯恒:還是要看電影本身,不過對我來說,能賣出去就已經很開心,覺得能賣到就感謝天,感謝地了,哈哈!
吳蕙君:這個問題是沒辦法一兩句話就能回答,我不知道這位觀眾是不是針對平台在問,那如果是針對平台、新銳導演來說,很多時候是一次性(One-off)的放映費,有的時候是平台要求買斷,例如剛剛跟各位提到的那個家傳戶曉的網上串流平台,他們不可能跟你說按點擊率計算(By click),況且按點擊率算錢的話,我們會不會得到一份誠實的點擊報告呢?我也不太確定。
郭斯恒:我也會好奇這些點擊報告真的是如實回報嗎⋯⋯
吳蕙君:我的經驗是能夠很清楚看到那個點擊報告的線上平台,只有iTunes做得到,Vimeo是使用者自己控制的,但其他平台都是在分銷,總合一個報告給你,本身的機制是不透明、不直接的。
曹柳鶯:我也同意,能夠賣出去已經很不錯了。
切忌為了影展去拍戲 不要只做「迎合」影展的導演
主持楊寶文:時間差不多,我們的對談也到尾聲,關於「國際發行」,在座三位可以給新導演一些建議嗎?
吳蕙君:去年我剛好當了金馬獎的評審,看了很多華語的短片,發現不止台灣,整個華語圈的導演都有很好的創作能量,很多作品令我很驚艷,有很多很有趣的案子。
短片是很好的起點,讓發行方很快看到你的想法和能力在哪裏,我會鼓勵新銳創作人多拍短片,盡量多關心業界的情報,然後把自己的短片讓更多人看見。
曹柳鶯:我想說國際的電影節和市場的確是重要,但作為創作者,可能在創作的過程中不要想太多這些事情,因為我看到很多,特別是來至中國大陸的導演,他們一直有這些想法在腦子裏,就是我這個電影拍完一定要去甚麼電影節,所以他的東西會很迎合,對我來說這個迎合的東西就只是他專門在拍一個電影節的電影,可能對電影節來說也是沒有新意的,還是要拍自己最想拍的東西,最後才有好的結果吧。
郭斯恒:對,在初期寫劇本的階段,的確有很多導演都會這樣想,我很少遇過導演是不在意影展的,通常這樣說的,都是騙人。
希望各位想清楚自己要說甚麼東西,自由的表達是很重要的,所以年輕的電影工作者可以在電影的各個製作階段,經常去問自己,「你最想講的是甚麼?」,往這個方向前進,不管有多少不同的聲音進來,你也可以繼續寫,繼續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