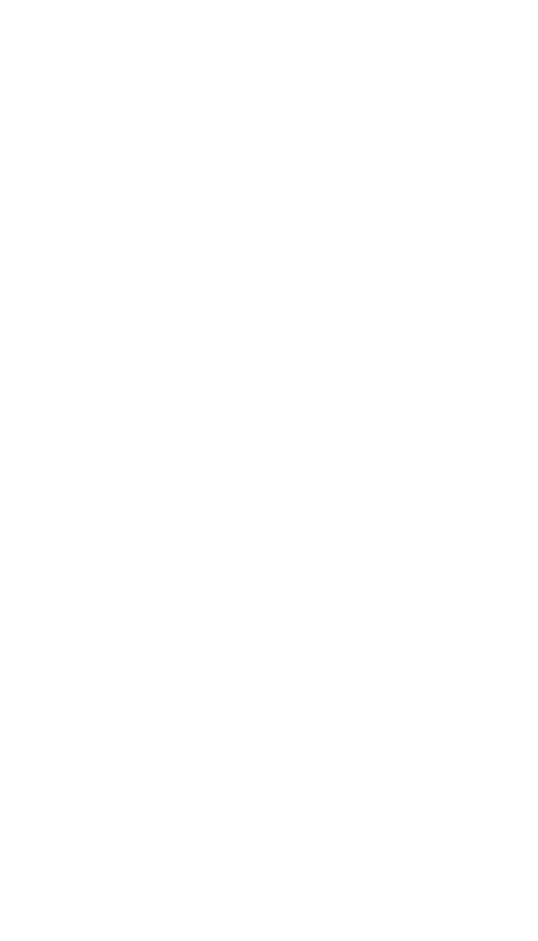泰國獨立電影的異彩
文:李駿碩
應平地映社邀請,我為主持「亞洲新銳電影製作生態」的其中一個研討會,一連看了5部泰國獨立片。當香港上一輩電影人在緬懷以前港產片強勢,能夠於東亞各國出口文化產業,並慨嘆當下今非昔比同時,他們有主動關注各地的電影生態嗎?
既然根本早已回不了去,我們又有破釜沉舟地前行的勇氣嗎?
平地策展的用心
這次電影節目策劃別出心裁,不是一般以作者或類型題材作為主幹,而是強調地緣與製作,關乎網絡與生態,不同主題包括跨國合資、後製及海外發行,這是在討論香港電影工業興亡之際的及時回應,我等來自香港的新進電影人,均抱着學習心態來參與是次跨地交流。
這次我負責的項目,是與兩名資深剪接師的交流,馬修與賈樟柯導演合作無間,也是華語片的常客,香港觀眾不會陌生。另一個是利查泰米提古,他是康城金棕櫚得主泰國導演阿彼察邦的御用剪接師,除了剪接,也會當監製,亦是同志片《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後製統籌。
剛剛過去這個月,我一連看了5部由利查泰米提古操剪接刀的泰國獨立片,實在大開眼界,分別是在今年鹿特丹影展奪得費比西影評人獎的《破曉有時》(The Edge of Daybreak ), 3部將會由平地放映的舊片《看似平凡的故事》(Mundane History )、《入黑之時》(By the Time It Gets Dark )、《重返天堂之城》(Nakorn-Sawan ), 最後當然還有重溫金棕櫚獎《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 )。
當中我對《平凡》與《入黑》尤其雀躍,因為兩部均由我剛剛在《濁水漂流》拍檔的香港攝影師梁銘佳掌鏡,導演是他在紐約念電影的同學阿諾查蘇維查康彭。
泰國學生運動的精神轉化
5 部作品中有兩部的主題是抗爭運動,《破曉》和《入黑》均串連了當下與1970年代的社運歷史,另外《平凡》和《波米》均以創傷作為喻體,同樣涉及社會動盪的後遺精神狀態。這些作品的表達方式都不是直接描繪激烈的衝突,或倡議性的宣示立場,而是經歷了年月的沉澱,以靜謐的凝視莊重地面對逝者,在歷史面前擇善固執。
他們的歷練以至精神轉化,也革新了這些作者的藝術表現形式。緩慢而凌厲的影像,處處滲透魔幻元素,也汲取了泰國強烈的佛教文化。他們的班底互相合作,作品互相呼應,早已成為一股浪潮,其藝術造詣明顯比我們高,在國際影展間也
得到了更大的成就和關注。
讓我拿《入黑之時》做例子,故事主線講述女導演為了拍攝法政大學大屠殺的電影,去訪問當時的倖存者,頭半段是作者與受訪者的交流,探討作者選以第一身或第三身敘事的權力思辨。而後半段則是演員在準備角色,進出演藝界的燈紅酒綠和戲劇中的悲慘歷史,同樣對自身產生了存在危機。
「戲中戲」的內容其實沒有直接向觀眾交代,或者是以多層敘事的剪接方式暗示了,社運中的豪言壯語,都化為了私密的個人情感,如此處理歷史反而更見深刻。看這些泰國獨立電影,最大的得着竟然是它們不注重交代歷史、交代劇情、交代人物結局,放棄了悲情與自憐,反而有顛覆傳統戲劇架構的力量。
只要自由 電影不死
這刻他們說「香港電影已死」,卻只沉醉於「復興」心態,官方的資助以至本土投資方,不論政治審查與否,其大方向只顧作品的商業性,申請與審批處處偏重傳統工業模式,進一步扼殺具革新性的藝術表達,即使不斷將1980年代電影業的成功商業方程式反炒重用,亦無補於事。
如何阿嵐上期所言,商業製作與獨立製作乃相輔相成,在缺乏官方資助的泰國如是,就算在如日中天的韓國電影業亦如是。2000年代在李滄東導演擔任韓國文化部長時,他推動國內院線獨立片配額,影院必須播放一定數量的本土獨立片,當時被主流影視圈強烈反對,但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整體民眾的文化修養因而提升了,試問韓國在2000 年代初若沒有出了一個又一個獨當一面的獨立導演,它的商業電影市場會有今天的外輸力量嗎?
歸根究柢,香港對於創作本身沒有信心,所以把希望押注在工業上。我不是說工業不重要,然而,就算沒有工業沒有院線沒有頒獎禮,都可以出產優秀的電影,世上多少地方如是;沒有真正的電影才肯定不會有健全的工業。
地下電影、手機電影、閉路鏡頭電影,這個年代老派新派層出不窮,只要電影是自由的,電影就不死。